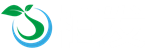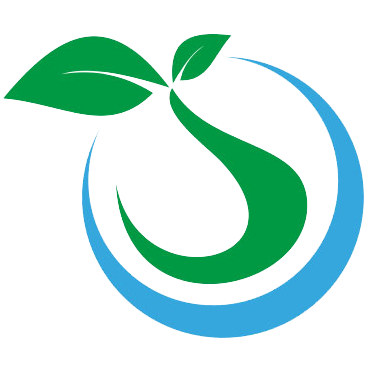《孝经·开宗明义》有言: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。”意思是身上的一切都是父母给的,绝不能有丝毫的损伤,指爱护身体如同敬爱父母。所以,我们要孝敬、尊重父母,当不在话下。孔子在《论语·里仁》又说:“父母在,不远游,游必有方。”因为我们是父母身体的一部分,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,子女要是走远了,父母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双亲是会心神不安的。我很信奉这两句话。

在我幼小的记忆中,年轻的父亲就有一头乌黑、油亮、细嫩却稀疏的头发。
那时,偌大的村庄没有一个剃头匠。男人剃发都是从外村请的剃头师傅。剃头的人,是十几里远的铁路埂村人,大家喊他“像师傅”。他与父亲差不多年纪,个头矮小敦实,标准的农村庄稼汉,剃头不过是他的闲余手艺罢了。一个乡间手艺人,家里同样种着十几亩田。每隔十天半月,剃头像师傅背着他那一身灰黑的行头,走村串巷到各家各户为男人剃发。剃头都是包年,平日不收钱,只吃派饭。碰巧,刚好在你家忙豁到已快中午或临近傍晚,就吃一顿派饭,谁家都不会推辞。工钱只等到年底结账。如实在手头紧张,等下年付清也是有的。乡人们都很淳朴,恪守着诚信二字,无人会赖账。吃手艺饭的,都会通情达理,知道各家的情况,实在周转不过来的东家,让他拖个两年。
不过话说回来,像师傅的手艺倒是一般,确实不敢恭维。
他给乡亲们剃的头,也是标准的乡下头,一看就土里土气,十足的农村味。更重要的是他出手比较重,可能跟他长期劳动有关。我们村男孩子因了大人的缘故,隔三岔五也会“享受”到像师傅的手艺。我们都被逼无奈,不然也不愿在像师傅面前俯首称臣。像师傅左手按着你——好像你不老实似的,右手拿着迟钝的推剪,“咔嚓咔嚓”替你剪发。长短不一的头发犹如鸟的羽毛往下掉。不知是推剪不锋利,还是手上拿捏不到位,推剪总是咬着头发根撕扯,有时好像要把头发拔下来似的,叫人生疼。这并不打紧,尤其是帮你修容刮汗毛的时候,飞快的刀从皮肤上耀武扬威驶过,带着寒光,大热的天,却一点儿也不冰凉干爽,却有一种热辣辣的灼痛之感。
一个夏天,五六岁的我熬不住僵硬呆板的身姿,头稍一偏,像师傅一不留神,手没按住,我便觉得脸上一阵火烧火燎的疼痛,原来脸上被蹭出了一道鲜红的长印子,不时渗出血迹来。我顾不得害羞,号啕大哭起来,边哭边使劲挣脱像师傅的手,跑得老远,气急败坏地说:“不剃了,不剃了!”一旁的母亲也有点怪像师傅下手太重。像师傅尴尬地搓着手,掸掸刀片儿,自圆其说:“还好,还好;不会,不会;没事,没事。”
以后,每次碰到像师傅,我都如临大敌,如履薄冰,战战兢兢。
但是,全村的大老爷们挺能包容像师傅的服务。
我父亲每次理发,坐在一把竹椅上,背往后伏下,头稍稍仰起,任凭像师傅的摆布。剃完头,另要刮胡须、掏耳朵,甚至剪鼻毛。
父亲因头发稀少,在像师傅的“铲土机”势不可挡的作用下,横扫千军,要不了霎时功夫,他的头发就短下去变顺了。便是刮胡须、掏耳朵费时费力。有过前车之鉴,我总担心像师傅手重,会不会把父亲的耳朵弄疼了。当看到大人们一幅闭眼享受的模样,担心也是多余了。
一直以来,父亲从不用洗发水洗头发。大热天,钻进港河里,任自然的流水洗濯,那叫一个痛快淋漓。平常也只是拿手巾擦擦揩揩,哪怕劳作过后,出了汗水或弄脏了头发,或头皮发痒了,父亲也只是打盆热水,将头发浸在脸盆里好好泡一下。根本不用那些化学的洗发水、洗发乳、洗发液、洗发露什么的,顶多也只是抹上香皂,再用水冲洗。不知是舍不得还是不喜欢,父亲总是说:“用肥皂洗头发好,干爽爽的。”
很多人在中年甚至青年,因受遗传基因的影响,年纪不大,就有一头白发,长得“仓促焦急”,我们称之为“少年白”。人未老,发已白,灰白相间。为了美观,众多人喜欢去染发。染色的头发看起来乌黑,却缺少天然的光洁,黯淡无光。若干时日之后,经过多次冲洗的缘故,头发颜色复原,灰白掺半,杂七杂八,煞是触目,惨不忍睹。
俗话说:“一白遮百丑”,皮肤白,能够掩盖人其他的缺点。人有一头秀发,亦是迷人的,女人是如此,男人也一样。电视中,洗发水的广告,离不开乌黑秀丽的头发作前缀。通常情况下,头发粗和密是相辅相成的,稀和疏是相得益彰的。
父亲头发稀薄的基因遗传给了我。每次去理发店理发,师傅会说:“你脱发还是蛮厉害的。”我也只是默不作声。更为好笑的是,到超市买洗发水,立马有服务员十有八九给我隆重推荐防脱发的品牌,搞得我异常尴尬。
值得庆幸的是,耄耋之年的老父仍然有着一头头发,虽然稀薄,却如当年,细嫩、乌黑。愿父亲生命之树常青。朱小毛